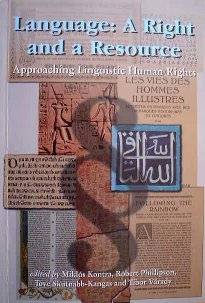
语言权也是人权
(书评)
Miklos Kontra, Robert Phillipson, Tove Skutnabb-Kangas, Tibor Varady. (Eds.). 1999. Language: A Right and a Resource. Approaching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346 p. ISBN 963-9116-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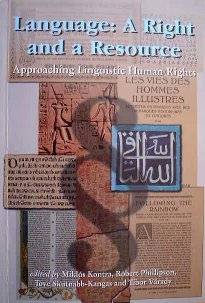 |
语言权也是人权 (书评) Miklos Kontra, Robert Phillipson, Tove Skutnabb-Kangas, Tibor Varady. (Eds.). 1999. Language: A Right and a Resource. Approaching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346 p. ISBN 963-9116-64-5. |
语言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暂且不论它结构上的神妙之处。就它在社会方面的作用而言,也是令人深思。为什么在有的地方语言是一种社会的“黏合剂”,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它又成了“分化素”呢?如果语言是一种“资源”,为什么掌握这种资源的国家和政府会拿出钱来极力让别人使用他们的资源呢?经济是驱动某种语言成为“谋杀”其它一些语言的“凶手”吗?如果说一种共同的语言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某些人难以割舍的“母语情结”?既然“语言权利”是人权的一种基本组成部分,为什么像联合国等最讲人权的国际组织在实际运作中却对此视而不见呢?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一幅扑朔迷离的图景,社会语言学家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本书就是一组学者从法律、经济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出发,以语言人权为核心,对诸如上述之类问题的探索。
正如本书的几位编者在开篇所言:许多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声称他们的语言人权受到了侵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民族之间的纷争时有发生。语言学家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理清语言在这些纷争中扮演的角色,进而提出构建一个更和谐未来的路径。(p.1) 编者的这一立论是非常重要的。长久以来,语言学家蜗居在自己构建的“精舍”里,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杰出代表”。虽然身处其中的学者无时无刻都在感受着“语言学”研究的妙不可言,但在局外人看来“语言学”无疑就是艰深、无用的“化身”。我们一直认为作为研究人类“智能”外化特征的语言学家,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对于人类本身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本书也可看作为语言学走向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题为“语言人权:概念及现状”的首篇文章中(p.1-21),几位编者简述了语言人权(LHR)的基本概念和中心任务;提出了从多种学科研究LHR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讨论了语言是一种问题、还是一种资源或者权利的问题。列出并分析了三种常见的限制语言教育的方式,鉴于语言教育是语言人权的重要基础,采用母语的教育权是LHR中的基本权利。事实上,语言帝国主义对于其它语言的侵蚀往往就是从语言教育开始的。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讨论,读者可以参考Robert Phillipson的专著"Linguistic Imperialism"(19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语言人权绝对不是一种局部的现象,它也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国际性问题。Robert Phillipson的“国际语和国际人权”讨论了国际范围的语言人权问题(p. 25-46)。作者研究讨论了如何有些语言会成为所谓的“国际语”,并拿英语作为例子简述了其成为“国际语”的历程;对于哪些声称基于平等基础之上的国际性组织的语言策略,作者认为仅仅使用少数几种语言作为正式语言这一事实,本身就侵犯了语言平等的基础。作者认为“国际语”本身就是与“语言人权”相冲突的。社会的发展需要“国际语”,但是人们又希望这种国际语不会侵犯自己的语言人权。正如我在评述一本关于“多语现象”的著作中所言,如何在保持五彩斑斓的语言和文化的前提下,使用一种共同的国际语,是人类的梦想也是对于语言学研究者及其他学者的挑战(Esperanto aktuell, 18 (1999). p. 10-11)。显然采用任何一种所谓的自然语言或民族语言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引入某种计划语言(也称人造语言)。我们高兴地注意到,Phillipson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注意到了计划语言 Esperanto (世界语)的这种语言人权和社会语言学功能。我们也相信,随着语言人权意识的增强和国际语言生态环境的净化,计划语言在人类的跨语交流中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例子说明语言人权不仅仅是纸上的东西,因为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所以从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中更能发现语言人权现状的真实情况。Miklos Kontra 的“不要在公开场合讲匈牙利语!”从民间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匈牙利语在几个国家的使用情况(p. 81-97)。通过调查分析,作者认为有下列三种常见的理由(1) 可理解性的理由; (2) 在 X 讲 X 语的理由; (3) “饲养”理由。从 Kontra 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问题在某些国家是非常尖锐的。因为,我本人目前也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根据个人的观察,至少在本地区没有发生 Kontra 文中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东西方的差异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社会权力结构如何在语言政策中得以反映?这是 Mart Rannut “共同语言问题”一文的主题(p.99-114)。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社会权利机构对于语言政策制定的影响。本文所指的“共同语”是国家内部的共同语。对于如何制定出符合语言人权的“共同语”策略,作者也有所涉及。
既然语言人权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听一听人权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一定是有益的。Fernand de Varennes 的“少数民族在国际法中的存在权”就是从现有国际法有关条款出发探讨语言人权的尝试。(p.117-146) 早在1000年前,匈牙利的斯特凡大公就意识到“一个统治者把一种语言强加到所有民众身上,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和软弱的表现”。遗憾的是,在这1000年里,有许多统治者不断做着此类蠢事。作者认为在历经1000年的发展之后,国际法终于认识到了斯特凡大公这句名言所含的智慧。现有国际法中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条款,至少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用来鉴别这种“愚蠢”行为的框架。
语言的扩散、维持和衰落一般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Francois Grin 的文章“市场力量、语言扩散和语言多样性”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p.169-186),特别是市场力对于语言发展的作用有精辟的分析。我们特别注意到了作者的这样几个观点:市场力对于语言的扩散有作用,但它不是语言扩散“万能”的或“惟一”的力量;没有阻挡的市场力会推进某些没有市场价值、经济价值语言的死亡;语言的市场价值不等同于其经济价值。作者认为语言之间现有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于政治、地缘政治、战争等方面的不平等造成的。我们认为虽然单一的市场和经济因素可能不能把某一语言的扩散推向极至。但是在其他一些因素将语言扩散到某种程度时,市场力对于这种语言的进一步扩散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讲,一种语言的消亡就是一种文化的消亡。语言的多样性、人权以及“自由”市场构成了世纪末一幅奇妙的社会语言学景观。Tove Skutnabb-Kangas 从世界语言状况开始,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与此相关的问题(p. 187-222)。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篇文章是本书的“重头戏”,值得特别关注。在分析了世界语言的状况之后,作者认为“今天许多语言正在被杀害,语言的多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也许我们会说:“哪又如何?这难道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吗?如果我们大家都讲一种语言和少数几种大语言,哪不是更方便了吗?”作者的回答是 “NO!”。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星球上,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消亡速度胜于生物多样性的语言多样性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为什么人们可以容忍发生在身边的语言“谋杀”,有时还心甘情愿被“杀”呢?Skutnabb-Kangas 试图通过语言的市场价值来解释这一现象。作者认为“如果人们被迫转换自己的语言,以求得某种基本生活之外的经济利益,那么这不仅侵犯了他们的经济人权,也侵犯了他们的语言人权。对于语言人权(特别是教育权)的侵犯,可能(已)导致民族争斗并削弱语言及文化的多样性”。我们认为 Skutnabb-Kangas 和本书其他作者对于“语言人权”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限于篇幅,我们没有谈及其他作者的文章和观点。本书的出版对于“语言人权”的跨学科研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书对于社会语言学、人权、语言规划、国际语学等领域的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人类语言现象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语言人权是一种人权,谈论人权的著作往往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但人权问题是否应该考虑哪些所谓“受害者”的心理感受呢?在读本书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大批为了生活的好一点而争相学习英语的人群。不幸的是这样的人群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难道这些人就不担心自己的文化消亡吗?本书是用“语言帝国主义”的英语写成的,而书中的作者的母语大多不是英语。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如果我们想知道这本书的内容,首先你得学习英语。而此时,你的语言人权何在呢?也许语言人权只是学者嘴里的又一种时髦的说法,但是语言交流、学习中无疑却是存在着不平等现象的。也许最为理性的做法是在保留母语的同时,人人都学习一种计划语言作为一种共同的第二语言。但是 Esperanto 一百多年的历史说明,这条路也是荆棘密布。甚至连职业就是语言的语言学家们,也极力反对这一最具理性的方法。语言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 Copyright, 1999, Liu Haitao |